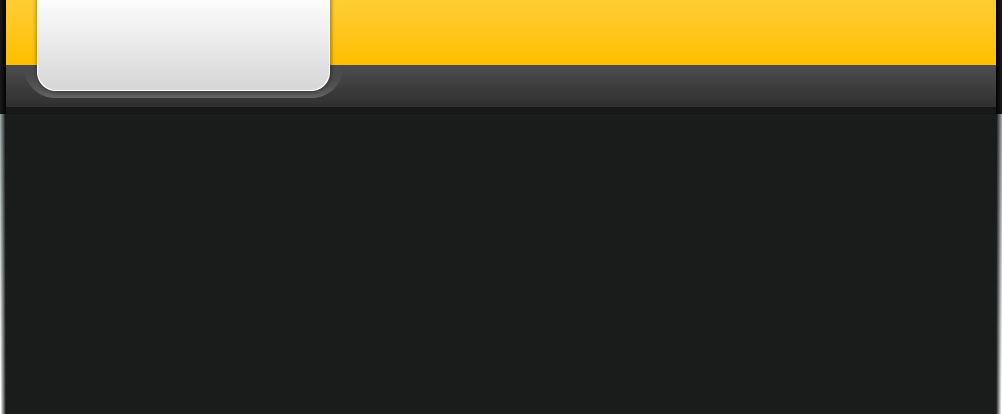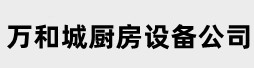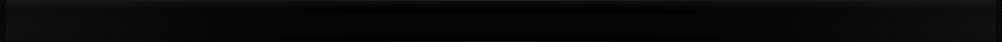首页〈优信网娱乐〉首页,蚂蚁集团如何重塑想象力?核心在于两张牌,一张是蚂蚁消金,另一张是钱塘征信。
这两张牌决定蚂蚁集团营收占比近40%、净利润占比过半、规模超2万亿的微贷科技平台能否平稳落地,甚至决定了蚂蚁拥有更大的想象力。但即便以让渡股份为代价,这两张牌打得依然不算顺利。
数月之前,四大AMC之一的中国信达宣布:拟不参与蚂蚁消费金融股权认购,原股东鱼跃医疗002223)和新股东舜宇光学也宣布暂缓投资。至今,蚂蚁消金的增资计划都没有新的消息传出。
据燃财经报道:“富达资产等外资不断调整后,蚂蚁的最新估值在今年4月已经降至500亿美元,相较IPO时的3200亿美元估值跌幅84%。”
对于蚂蚁而言,当下有两件事至关重要,其一就是消费金融牌照增资是否顺利,这直接关系到2万亿信贷资产能否成功继承;其二是钱塘征信的设立,成功与否决定了未来蚂蚁集团是吃肉还是喝汤。
本文以《蚂蚁集团如何重构想象力》为题,但要探究蚂蚁集团如何重构想象力,就必须知道蚂蚁集团的想象力源于何处?以及蚂蚁集团是如何失去想象力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支付、账户体系也可以是10亿级的活跃用户或者万亿级的信贷资产.....当然,更可以是数据。
市场好的时候,比谁冲得快;市场不好的时候,比谁跑得快。——某金融科技公司高层
2013年6月13日,余额宝正式上线发布,时任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国内事业群总裁的樊治铭在会上说余额宝是“金融行业的一小步,互联网行业的一大步”。
很多人站在“亲儿子”的立场上声讨余额宝,但如今天所见,这个现象级的产品没有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反而成了银行业身后的“狼”,不断催促它们创新。
余额宝之后,花呗、借呗陆续上线,蚂蚁虽然不是银行,却拥有了银行存、贷、汇的核心功能,再加上它与阿里电商以及线上、线下各种消费支付渠道的强绑定,海量数据603138)沉淀了下来,一个以支付为核心的数据帝国逐渐成型。
2017年,趣店IPO将小额现金贷(也就是714高炮的前身)推向风口浪尖,舆论大有失控之势。
穷人们的财富被现金贷平台收割,而他们的数据则源源不断地充实了蚂蚁集团——芝麻信用与大量小额现金贷平台有数据合作。
就在强监管来临前夜,芝麻信用与大量现金贷平台停止合作,2017年11月21日,据一家现金贷平台负责人消息,终止合作的理由是“自贵公司与芝麻信用合作以来,芝麻信用持续收到多起用户对贵公司存在收取法定保护利率以上各类费用、不当催收等方面的投诉。”
那一年,支付宝账单疯狂刷屏,不少人发现在查看账单时,会默认勾选了“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该协议中涵盖“您(作为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理解并同意,您同意第三方查询您的非贷款类及其他非涉及商业秘密信息时,我们可以直接向第三方提供您的信息。”等大量涉及用户个人数据的条款。
在数据上,蚂蚁的擦枪走火不是特例,它的老对手京东科技(原名:京东数科、京东金融)曾投资一家名为聚信立的数据公司,这家公司于2019年卷入套路贷风波,京东数科除了是聚信立的股东之外,也是它的重要客户。
蚂蚁集团凭借一些正常、正确、强大的以及一些大众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数据帝国。
2017年,蚂蚁发生了一次“从Fintech到Techfin”的大转向,“改变银行”这朗朗上口的四个字成为现实后,矛盾双方逐渐从竞争走向竞合。
不少银行对于蚂蚁的合作有所不满,但又无可奈何,资产和数据都掌握在蚂蚁手里。
IPO前,蚂蚁金服想打科技概念,一方面将支付宝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另一方面改名蚂蚁集团,事实上它也成功了,虽然只是在资本层面。
若以银行、保险以及金融科技行业普遍10倍以下的PE计算,蚂蚁集团的市值不足5000亿元,但在IPO前蚂蚁集团市值达到了2.1万亿元。
而在舆论层面,市场对蚂蚁集团的定位产生了两极化的声音,包括笔者在内的“正方”认为蚂蚁集团的科技定位十分坚固,而多数“反方”则认为蚂蚁集团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甚至是一家金融公司,原因是微贷科技平台为其贡献了近40%的营收,加上理财、保险科技平台,超过63%的营收都是来自于金融业务或服务金融机构。
一个可以支持“反方”观点,但却被忽略的数据是:蚂蚁集团微贷科技平台主要由两家小贷公司和两家科技公司组成,均为蚂蚁集团全资子公司,这四家公司在2020上半年的净利润是多少呢?接近113亿元,而同期蚂蚁集团归母净利润约212亿元,亦即在蚂蚁集团过半净利润都是微贷科技平台提供。
蚂蚁集团IPO前,组成其微贷科技平台的四家全资子公司的净利润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家小贷公司净利润暴跌,总额不过10亿元,而蚂蚁智信、重庆万塘两家为信贷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的净利润较2019年全年增长了一倍多,总额超百亿元。
从表面上看,这是利润的腾挪,但从本质上看,蚂蚁集团的印钞机——微贷科技平台核心竞争力的载体并不是两家小贷公司,而是蚂蚁智信和重庆万塘,当然两家科技公司也仅仅只是载体而已。
整个蚂蚁集团衍生出的资产和它过去十余年不遗余力构建的数据帝国,才是微贷科技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一点,从蚂蚁的募资用途上也可以看出:其承诺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额贷款等不属于一行两会批准设立的持牌公司从事的金融业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或到位36个月内,除为满足监管政策或要求外,不再新增对一行两会监管体系外的类金融业务的资金投入。

马云是搞平台经济的,他的蚂蚁集团搞的是金融业的平台经济,但金融业本质是杠杆生意,要想多赚钱,就必须承担杠杆带来的风险。
情况已经这么差了,还有可能更差吗?拼一下,万一监管和当年容忍余额宝一样容忍信贷呢?——这或许是某位大人物上台演讲前的心理。
虽然微贷科技平台从净利润的角度已经“科技化”了,但两家小贷公司的战略意义依然重大。
不同于电商,金融是特许行业,需要持牌经营,但持牌只是开始,比如今天的蚂蚁消金虽然是持牌经营,但仍迫切的需要增资。
如果网络小贷业务的杠杆受到了限制,那么营收占比超40%、净利润占比过半、余额超2万亿的微贷科技平台就会受到影响,整个蚂蚁的基本面都会不稳。
坊间一直传闻,在文件正式落地前,马云等高层就看到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于是才有了马云在外滩的疯狂输出。
这次演讲引发的舆论几乎一面倒——怒批马云和他的蚂蚁,随后蚂蚁上市计划暂缓,至今没有太多消息。
2021年上半年,央行等部门陆续约谈了蚂蚁集团和13家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针对它们普遍存在的无牌从事金融业务等问题,提出自查整改要求。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无差别打击,但事实上2021年的金融科技行业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蚂蚁集团,另一个世界则是蚂蚁集团之外的金融科技公司,腾讯金科和京东科技则尴尬的漂浮于两个世界之间。
在某金融科技公司工作的张明表示:“巨头释放出的市场份额很大,现在风控只有评估最优质的客户才能拿到贷款。”
一些发力较晚的金融科技公司业务不过百亿元级别,这意味着蚂蚁集团即使只释放出1%的存量,都足够让它的单一友商业务成倍增长。
笔者在《蚂蚁,气虚,筋骨强》一文中写到:蚂蚁集团的根基是用户、数据和流量,而这些不是信贷业务带来的,而是以支付、生活、金融科技的整个生态带来的,信贷业务只不过是蚂蚁的变现方式。
对于第一个解决方案,其实蚂蚁的微贷科技平台一直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让网商银行承载这部分业务”,但若是这么做,蚂蚁收益只能有30%。
退而求其次,含金量比网络小贷更高、收益比例比网商银行更高的消费金融牌照就成了一个断臂求生的方案。
蚂蚁集团占消金公司股权比例为50%,虽然收益比例大幅降低,但相比于服务银行,蚂蚁消金自己放贷会承担更多风险,自然也会分得更多蛋糕,并且蚂蚁消金会不断增资,总收益说不定可以与整改前持平甚至更高。
一切看上去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意外如期而至——刚开年,中国信达、鱼跃医疗等机构认购蚂蚁消费金融股权计划生变。
有媒体曝出:我国的相关国企、银行等已经接到了通知,将对蚂蚁集团的相关业务进行新一轮的全面排查,目的是查明这些国企对蚂蚁集团的投资及其他关联。
据第一消费金融:知名消费贷巨头A公司持续在被限制消费贷管理规模,目前,A公司通过旗下消费贷产品B和产品C管理规模已经降低到万亿以下。监管对该公司的管理规模预期,第一目标是降低到3500亿元。
2021年7月,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给网络平台机构下发通知,要求网络平台实现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连”,过去的无冕之王“芝麻信用”不可能继续裸奔,形势比2020年外滩峰会后更加严峻。
以蚂蚁的实力,参股个人征信牌照不是问题,但问题就出在“参股”这个性质上。
在2015年,芝麻信用等八家机构曾一起申请个人征信牌照,但三年之后2018年1月,却传出百行征信获批的消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为最大股东,之前的八家机构均未获得牌照,仅在百行征信各持股8%。
这种“不愿意”背后的逻辑很好理解,股权比例也是收益权的比例,腾讯与蚂蚁的数据量与其他小股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权利与义务完全不等价。
2020年,读懂数字财经曾发布独家文章:《花呗数据正逐步接入央行征信 未来将覆盖全部用户》,文章中指出: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的“迟到”不是个例,不少互联网巨头的信用付产品也选择了“迟到”,比如京东数科也是在2019年才开始分批接入央行征信。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巨头过去消费分期业务的体量小,是否接入征信监管也无所谓,后来规模太大了,就开始有了入征信的压力,只能采取分批入征信的方式。”
结果这从2019年就开始逐步接入征信的举动,到2021年还没有结束,2021年9月再次爆发了一波“花呗入征信”的报道。
巨头们对于“入征信”的抵触不无道理,一方面入征信会影响一些用户的体验和使用意愿,降低竞争力;另一方面数据是宝贵的资产,尤其对于信贷业务而言,入征信则意味着巨头的数据要与所有金融机构共享,而收费方也会变成个人征信机构而不再是巨头。
百行征信之后成立的朴道征信同样是国资占大头,由北京金控作为第一大股东,京东科技、小米等公司持股比例在后。
2021年11月26日消息,央行受理了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据央行公示的附件信息:钱塘征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十亿元,蚂蚁集团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同为35%。
从明面上看,蚂蚁与国资占股相同,这已经是开了先河,但第三大股东却给钱塘征信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
杭州溪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钱塘征信的员工持股平台和第三大股东,该公司的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56号阿里中心4层C段402-9;其次,杭州溪树大股东与网商银行监事会主席都叫董占斌,小股东与蚂蚁金服一位投资经理都叫孔令仁,这是否是巧合尚未可知。二人拟任钱塘征信总裁和财务负责人。

若二人皆出身于网上银行、蚂蚁集团,这背后的利益格局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蚂蚁集团可以持牌经营、获得更多利益,这些数据也可以去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发光发热。
《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第九条也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自受理个人征信机构设立申请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并根据有利于征信业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的审慎性原则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依法颁发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
很明显,去年11月就申请成立的钱塘征信早已过了“60日”的时限,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谁都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蚂蚁集团重塑想象力的两条路都很坎坷。信贷遭遇打击后,蚂蚁集团的盈利能力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1年第三季度,媒体以阿里巴巴财报推算出蚂蚁集团2021年第三季度净利润约为176.09亿元,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蚂蚁集团三季度净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受投资收益影响:印度生活服务平台Zomato和印尼电商企业Bukalapak。
有市场人士评价指出,蚂蚁集团作为早期投资者,在Zomato和Bukalapak分别持有14%和13%股份,即使保守的按照一倍收益来计算,去年7-9月蚂蚁从两家公司获得的账面投资收益可能就有60多亿元,该人士据此估算出蚂蚁当期的经营净利润规模远低于根据阿里财报计算的数字,实际净利润环比或下降超过40%。
笔者也进行了一番计算后发现:三季度两家外企为蚂蚁贡献的投资收益恐怕比分析人士预计的更多。
且四季度Bukalapak股价遭遇腰斩,这意味着四季度该公司不再是蚂蚁集团业绩的助力,反而可能会拉低蚂蚁四季度的净利润。(欲了解详细情况,请阅读《Bukalapak去年四季度股价腰斩,会拖累蚂蚁集团下季度的业绩吗?》)
总结来说,若不论投资收益,2021年第三季度的蚂蚁业绩在变糟,四季度可能更糟。
蚂蚁集团聚合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打工人”,他们之上是一批能力强悍、资源背景深厚的高管,很难想象有什么商业问题是这种商界梦之队无法解决的。